一
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条路,通向远方,连接故乡。在一去一来之间,经过乡愁的浸润洗礼,人生便厚重沉淀,精彩起来。
父亲张玉玺、母亲赵永生都是极其孝顺之人。从我记事起,就时常被这样一条路牵引着。每年春节,我们全家都要融入回乡探亲的滚滚人潮中。那是一个旅途充满艰辛的年代,没有高铁,没有高速公路,只有慢吞吞的长途汽车和绿皮火车。

作者的父亲与母亲
从清水河县出发时,全家人穿上最干净整洁的衣服,先坐长途汽车到呼和浩特(简称呼市),然后坐火车到集宁,再从集宁坐长途汽车到丰镇县隆盛庄镇。
童年的记忆中,春节回老家会见到很多亲戚,会有很多好吃的,但这也意味着,不知道翻了多少座山、穿了多少条沟、过了多少条河。那山重水复带来的苦和累,常常让人想哭。
从清水河到呼和浩特这一段路,山大沟深,坡陡弯急串起一个比一个险峻的地名。过了和林县,有一大段盘山公路是著名的“九曲十八弯”,成为回家路上最大的障碍。
啊,蜿蜒逶迤九曲十八湾,是黄土地的“纹身”,是通天的路标。山有多高,路有多高,这条回形针一样的山路惊心动魄,如同银蛇一般纵横交错,一面是刀劈斧削的峭壁,一面是望之胆寒的万丈深渊。到了惊险处,父亲就会用手挡住我的眼睛。
数九寒天,路面结冰,湿滑难行,一路上时常见到滑倒在路边的车辆。有时大货车后轮滑出路面,深陷在路基大坑,堵住一长串过往车辆。好几次,为了救助路边的车辆,父亲他们这些精壮的男子汉就会从长途汽车下来,先固定好防滑铁链,再用铁锹麻袋去铺路垫路,最后众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一起推车,等上车时已是全身冰水和泥雪。
道路坑洼不平,一路颠簸起伏。我们坐在拥挤的长途汽车上,就像一叶小舟颠簸在大海里,五脏六腑都快要被抛出来。破旧的汽车绕着一圈圈的盘山路喘着粗气,行驶在高低不平的沙石路上,时而把人抛起,头顶撞到车顶,时而又向下急坠,如坐过山车,一趟车下来个个蓬头垢面,脸色难看,不少人都会晕车呕吐。我肯定是其中最年幼的一位,脸色煞白,
翻江倒海,恨不能把胆汁都吐出来。过年穿的衣服也弄脏了,回乡的激情早已被阵阵颠簸扔到九霄云外。
这200 多里“搓衣板”路,让小小的我望而生畏。坐车前,母亲都要给我准备一个塑料袋,收纳吐的脏东西。为了防止晕车,父亲母亲穷尽了各种办法:一路不敢吃食物,在我的嘴里含茶叶,往肚脐眼贴胶布……
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直到有一年,母亲的同事推荐了一款进口的防晕车药,好像叫“艾莫尔”,这药是成人药,大人吃一片,母亲给我吃半片,终于遏制住了这个烦心事。
在汽车上,百无聊赖间抬眼望去,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灰黄色,也许是造物主打了一阵长长的瞌睡,把所有的灰色和黄色都倾泻在这里,满目单调,好不荒凉。扶窗不知道张望了多少次,怎么没有一点绿色呢。偶而看到路边的一间公路养护工人的小屋,山顶的一座烽火台,都会让你的精神抖然一振。
二
那年月,绿皮火车绝对是高大上的交通工具。永远喧嚣的站台吞吐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把离别的篇章一再推演。列车呼啸而去,人群渐趋模糊。绿皮火车割断时光,又聚集时光,日积月累,循环往复,沉淀成人们挥之不去的凝重而温情的记忆。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两个心酸的曾经,郁结在心,成为不能释怀的执念。小小的我,已经对旅途的艰辛有了切肤的理解。
好不容易从长途汽车下来,转到绿皮火车,情形变得更糟。那是1976 年,我第一次在集宁中转,一切都觉得新鲜。出站时天已经漆黑一片,旅客们肩扛手提各种行李包裹从一个窄窄的通道出来。我被喧闹的人群挤散了,拉不到母亲的手,慌了神,“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对这座城市的初次印象,小小的我感受到的是紧张和不安。
呼市是省会所在地,始发车较多,从呼市到集宁这一段路相对好些,而从集宁回到呼市则永远是一场“恶仗”。春节过后,从集宁回呼市都是过路车,挤车的人多,几个后生保护着我,严阵以待,拼命挤车。
我一般是从窗口被塞进去,经常性的实战也让我从小练就了一副挤车本领。那时候,挤掉帽子、挤丢鞋子、少两颗衣扣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
集宁是出名的“大风口”,春节期间气温零下 20 多摄氏度,父亲瘦俏的背影走在前面,左手右手两只大包,里面各装 50 斤面粉,却能在熙熙攘攘的站台上健步如飞。还不忘嘱咐母亲,“拉好小虎,小心挤着”。
我呢,冻得红红的小脸,用一双稚嫩的小手,紧紧牵着母亲的大手,叠着步小跑,担心被挤丢了。
如果赶不上转车,就只好在集宁住下。年幼无知的我,总是搞不明白为什么火车都是绿色的?要是有其他颜色有多好。便问母亲,母亲转向父亲,这时候极度疲惫的父亲已经进入梦乡。
奶祖父田占元在集宁火车站的三轮社上班,是一位踏实肯干的老职工,也是集宁市劳动模范。我们每次转车,都会在三轮社候车。休息室在火车站旁边,屋中央置一小火炉,上面有个大茶壶,永远热气腾腾,保证师傅们一进门就可以喝上热水。只要老人家有时间,就亲自接送我们。
一年春节,在拥挤的站台上,四叔国营举着我,上面的旅客帮忙拉我,我的手高高举着,准备上车。
列车员的脸就像天色一样阴沉,没好气地大声嚷嚷,“不能上了,不能上了,等下一班吧。”“咣当”一声,踏板被重重扣下,列车门关上了,门框上冻的冰雪扑面而来,冰屑雪沫直从我的脖子、袖口钻到身体里,刺骨的冷。
“当心孩子的手,当心孩子的手!”人群中,那是父亲的咆哮呼喊。
父亲平素温文尔雅,那天却声嘶力竭,着实把父母亲吓坏了,害怕我的一双小手被门挤伤、砸断。母亲不顾一切冲过来,紧紧抱紧我,手再没有松开。
绿皮火车缓缓启动了,哐啷哐啷地抖落一身风雪……
三
如果没有经历过,很难想象当时挤车的这种情景,旅客们大包小裹如同难民,返乡的新衣服经常被挤破刮烂,鞋子挤掉也是常事。这班车上不去,只好等下一班,也许是半天后,也许是明天,回不了家,还得就近住下。
那个年代,交通不便,“铁老大”很牛。无论大站小站,火车都会停下。火车时速 60 公里,车轮与钢轨的磨合与撞击声清脆而响亮,“哐当哐当”向前缓缓行进,不像今天的高铁,安静平稳、舒适宜人。好不容易挤上车,车内的景象更是惊人。我不相信自从火车发明以来会有哪个地方曾经如此密集地装载过活生生的人,处处都是摩肩接踵,不再有过道和车厢接
合部,原先的厕所里塞满了人。没有人坐着,也没有人站着,至多只有一只脚能够着地,大伙拥塞成密不透风的一团,行李架上、座位底下,也横七竖八地睡着了几位疲惫的旅人,其情形犹如“叠罗汉”。实在没有办法,乘客需要从车窗进出,像一件包裹被人搡进去再被人推出来。
车厢里的乘客南来北往,嘈嘈切切地演译着各地方言。烟味、干粮味、汗臭味,还有七七八八的五味杂陈,大人的抱怨、小孩的哭闹、列车员的叫卖声,在鼾声和汗臭的包围里,汇聚出一曲热闹非凡的春节返乡奏鸣曲。火 车头伴着沉重的“扑哧、扑哧”声中启动了。在漫长的旅程中,吆五喝六的打牌声,谈天说地的喧哗声,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消磨这无聊的车程。
有了上次教训,父母亲以后再也不敢买硬座了,索性就超预算买一张卧铺和一张硬座,卧铺车厢人少,方便上车,让母亲带我走卧铺一边。
硬座车厢人多,上下车的旅客总是人山人海。父亲一个人带着东西在拥挤的硬座车厢左右腾挪挤来挤去。直到今天,都很难想象,并不壮硕的父亲如何在熙攘无比的车厢中捱过一宿直至下车。
人就是这样,一路上疲惫不堪 , 昏天黑地。可是到了家,看到亲人们的笑脸,路上的难受和不快全都是过眼烟云了。
假期结束又要往回赶,年年如此,周而复始,每一次都像是“打仗”,在北风呼啸中,我们全家挥汗如雨,紧张异常,一路颠簸,一路呕吐,一路刺激!
四
一切为了年节,目标就是故乡。
从呀呀学语开始,哐啷哐啷地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好多趟。由此,从小就害怕乘绿皮火车,坐长途汽车。
幼小的内心深处,也萌生出童年的梦想。到集宁,坐上绿皮火车回故乡。就在我的心田里,与思乡的激情还有拥挤的火车交织在一起。集宁这座城市,从此便成为我从清水河县、卓资县到故乡的一次次行程中重要的中转站。
一张张火车票,记录着我们家与乡愁之间的起承转合。
有一次,从集宁坐乘火车到卓资县,我和五叔都没座。我曾学过两年武术,索性扎个马步消磨时间。这时候,后车厢传来一阵一阵喧闹,是一伙从赤峰放暑假回来的大学生在打牌消遣,他们一会儿蒙语,一会儿普通话,一边打牌一边嘻闹,一路笑语欢歌,令人特别羡慕。原来这就是我心目中向往的大学生,多才多艺,潇洒活泼。
从此,心里暗暗地许下心愿,我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
十八岁,我也如当年的父亲一样,坐上绿皮火车,怀着懵懂梦想,去奔赴南京这样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城市上大学。这意味着成长,原先过往的一切要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未来是一张等待双手去绘就的白纸,没有划痕,没有色彩。
成年后,绿皮火车早已渐行渐远,慢慢被自驾、高铁和飞机取代,或远行、或归家,心中充满了思念和憧憬,也有疲累和无奈。(本文来自中华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的《父亲的手》)

本文转自公众号《三义泉文化苑》,作者张海东,教授,博士。现在中国气象局工作,曾任局长秘书。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财政部、工信部和故宫博物院等文化项目评审专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党史研究专家,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等,高校客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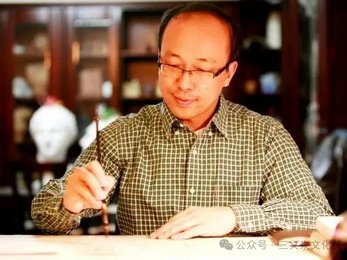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742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7429号